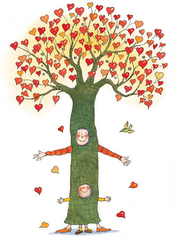但你還是來了
長年的疾病相隨 你開始一邊求助 一邊不相信一切可以改變
但你還是來了
習慣於替別人著想的你 敏感於他人的眼光的你 已經逐漸忘記了原來可以放輕鬆的依靠別人
你想盡辦法質疑著眼前的人 希望這個人的無能可以驗證你終究只能靠自己的孤單
但你還是來了
你的世界由你所創造 即使痛苦 但畢竟是屬於你自己的
你是被禁錮在自己苦心建立的城堡裡面的公主
一邊呼喊著救命 一邊阻擋著任何人來毀壞你的心愛城堡
最後只能獨自躲在角落啜泣
我希望能和你一起找到那把鑰匙 然後由你來決定你要不要打開門讓自己自由
或許你到時候還是會想要再次將鑰匙丟棄 把鑰匙藏在更難找到的地方
但我也要你知道 那是你的選擇 我會尊重你
只要你願意過來 我們都將有機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