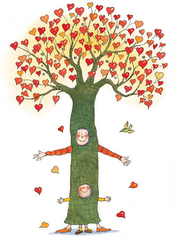有一天 情緒極差的摯友對我說 :
"我需要的只是你聽我抱怨 , 我不需要你像個心理師一樣告訴我應該怎麼想 !"
聽了很傷心
當時我自暴自棄地想 : 這就是我唯一會的關心人的方式 ,
原來這反而讓我跟朋友的關係變遠
好像這真的是一種"職業病" 甚至是一種"殘缺"
就像 : 如果你要當相撲選手 你只能那麼胖 你只會相撲
喪失了跟一般女孩一樣 討論簡單卻愉快的流行美容訊息的能力
也憤憤不平地想 : 老娘用盡心力幫你釐清問題 ,
原來你只想跟那些不經思考就跟你一鼻孔岀氣的人
一起製造更多思考垃圾 呼 !
半個小時內 , 非理性信念在我腦袋裡放煙火似地亂炸
煙火秀後 , 我與自己有些對話 :
"我不該把朋友當個案一樣看待"
"但是 如果我認為那般對待個案 是出自真心為個案著想的做法
為什麼對朋友反而不這麼做呢?"
於是, 我開始想像 假如換成是一個個案在治療室中跟我哭訴 我會怎麼做 ?
我發現 ! 我會安靜地聽他說 ! 全心地同理他 ! !
原來 , 面對好朋友的情緒 我還無法做到客觀 不動搖到自己狀態的境界
我太急著想幫他解決問題 為他的問題感到焦慮 反而無法接納他當時的情緒
-----------------------------------------------------------------------------------------------
另一天 另一位好友沮喪地跟我訴說她對未來人生的悲觀預期
不知是當天我狀況好? 是我倆生活緊密度較上一位低? 或當時他情緒較上一位平穩?
我能夠放下自己對他認識將近15年的主觀印象 像認識一個全新的人一樣地
不魯莽 不心急地 把我從他話中聽到的feedback給他
思考中完全不涉及過去15年中的 "我" 和 "他"
結果比我預期的好 (或者說 我完全沒有任何預期)
他給我的回饋是 : 我跟其他朋友說的時候 , 可能因為他們認識我 ,
所以會用刻板印象來看我 , 只會跟我說"你想太多了"之類的
跟你談過之後 第一次覺得了解了自己的想法
----------------------------------------------------------------------------------------------
"身為心理師 我能比個案的朋友帶給他們的更多嗎 ?"
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像感冒的時候
你需要醫生給你開藥
也需要家人或朋友給你安慰 甚至一堆來路不明卻滿溢愛心的偏方一樣
"身為心理師 我能比其他人帶給自己的朋友更多嗎 ? "
很遺憾的是 :
現階段的我 似乎暫時難以升任提供愛心偏方的單純快樂角色 (或許還需要一些自我突破)
但至少可知的是 :
如果我能克服急欲幫助朋友的私心 確實有機會為朋友奉獻我的專業
就像外科醫師要幫自己的家人開刀 或許需要更高的心理強度吧 !
2008年1月17日 星期四
心理師能比朋友給得多嗎?
跟朋友抱怨,反而讓人更沮喪?
節錄自 優活健康資訊網╱uho 編輯部 2007-12-28 12:12
相信有不少人有類似的經驗,當遇到不開心的事情,如果能找到一位了解自己的朋友傾訴,往往會明顯感受情緒的提升。相反地,如果傾訴的對象不同,卻有可能得到反效果。這是什麼道理呢?原來這不是心理作用而已,而是與不同的對象傾訴,的確對大腦產生不同的結果。
【向朋友抱怨的潛在危險】在最新一期的發展心理學月刊刊登了美國密蘇里倫比亞大學針對813位學生所作的研究,指出一項驚人的事實:經常跟朋友抱怨,反而會讓人更沮喪,而且這個現象發生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嚴重!這個發現似乎與我們所認知的關於「友誼」的功能背道而馳。朋友的重要功能之一不就是自己心情不好時能夠聽我們訴苦嗎?
主持這項研究的心理學家發現,無論男女當遭遇到問題時,通常都喜歡找朋友訴說這些困擾。但是如果這些耗盡漫漫長夜的促膝長談或昂貴的電話帳單持續六個月或更久,女性焦慮以及沮喪的情緒則明顯惡化,而男性的焦慮以及沮喪的情緒雖然沒有惡化但也未見任何改善。
這項研究並未指出朋友之間抱怨,其實隱藏著更多的潛在危險性。在數千個小時與個案的隱密對談中,聽到比一般人更多朋友之間「善意的傷害」。
【有效的談話是隱形的腦部手術】現在借助最新的腦部功能攝影技術,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和朋友聊天」與跟「和治療師協助下有效的談話」兩者之間,所造成腦部活動的不同!
根據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一群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引發30名受試者的情緒反應並觀察他們的腦部活動變化後,發表的最新研究發現:「將自己的模糊感覺用精確文字表達出來後,有助於調節腦部控制情緒的中樞以及右前額頁皮質的活動。」其他相關的研究也指出,長期進行心理諮商的憂鬱症病人,其腦部神經連結與未接受心理諮商的憂鬱症病人顯然大不相同!
換句話說,有效的談話(例如與訓練有素的心理師進行心理諮商),就像是替大腦作了隱形的手術。透過這種實證有效的方式,可協助將自己的情緒精確地表達出來,其結果不僅可提升自己的心情,也可避免一時的情緒衝動轉變成行動,而導致日後的悔恨。
2007年10月29日 星期一
【轉貼】然後我去看了心理醫生
我可以理解你的吃驚與訝異。因為在台灣〔註〕,大多數的人(就連我自己也是)對心理諮商是相當陌生的,總會以為非得要有什麼重大心理疾患,比如說精神分裂、憂鬱症、躁鬱症、甚至自殺行為等,才有「必要」去看心理醫生(這裡的醫生指的是心理諮商師)。而事實上,我的困擾與憂鬱真的不是什麼大問題;是啊,我即使睡不好但也不至於失眠,即使食慾不振但也不至於營養不良,即使憂鬱但也不至於自我了斷。我甚至比較擔心,這樣的狀況尋求心理醫生的協助,是不是太浪費醫療資源了?嗯,好吧,我或許可以這樣為自己辯護:如果醫療的定義是促進/維持個體之健康,而健康的定義是生理與心理雙方面的健全狀態,那麼,感謝我那極欲擺脫的憂鬱,我的確有看心理醫生的權利與必要。
但是也因為如此,老實說,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其實很抗拒面對心理醫生;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向他描述我的問題。我不能說:「醫生您好(其實應該是叫心理師,但是我已經習慣叫我的心理師作醫生了),我失眠,或是我有精神分裂或憂鬱症,請幫助我」作為開頭。我沒有這樣的問題,我的問題就只是一般人的、一般程度的憂鬱與傷悲,因為這樣就跑來看心理醫生,多少覺得情何以堪。
第一次會面
然而事實證明是我想太多了,第一次會面比我想像得還要順利。其實,只要當你開始說明(或是抱怨)某件讓你煩心的事之後(不管那件事是多麼地小、多麼地瑣碎,只要它是一件會讓你在意的事),你就會忍不住將所有的煩悶與不如意一股腦地全部吐出來。你會發現這短短的一、兩個小時的時間根本就不夠你抱怨,因為光是向陌生人抱怨、大吐苦水,本身就有一種令人無法自拔的神奇療效。當然,前提是這位陌生人要是一位很好的傾聽者,並同時展現最大的同理心與包容心;因為在面對困擾與情緒時,我們自己就已經感到莫大的衝突、不協調甚至是自我指責了,實在不需要找另一個人來數落我們自己的不是。而也正因為如此、因為不需要擔心被人責備,我們才能真誠地將自己的困擾說明白。其實,我們本來就應該真誠地述說自己的狀況。接受諮商本來就是想尋求一些協助,想真誠地面對自己、了解自己。如果一開始就抱著「他一定沒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的心態,那麼諮商也只是在浪費自己和醫生的時間;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好抱著「他一定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的預設,因為這也只是增加自己的心理壓力與負擔。我自己覺得,事情會不會好轉、諮商有沒有效果,多少取決於某種程度上的緣份;心理諮商只是為我們多開一扇窗,讓我們有一個機會用另一個角度來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所遭遇到的問題,(而擺脫自溺),如此而已。
有經驗的諮商師早已訓練出極其敏銳的嗅覺。他們看似靜靜地坐著、傾聽你的困擾與抱怨,腦子裡卻不動聲色地針對你的問題,快速地進行資訊的整理與歸納。當想到什麼可能性時,他們並不會武斷地說:「嗯,我覺得你的問題一定是…」或是「對,這樣的現象就是…」,而是再用另一個問題,詢問你的想法與意見。例如,正當我把我的問題一股腦地丟出來時,醫生卻突然問我:「你覺得你是個有自信的人嗎?」我怔住了,支支唔唔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沉思之後,我突然發現,原來這就是自己問題的根源:我並不是個有自信的人,我太需要別人的肯定與認同,而這深刻的慾望不僅左右我的行為、態度與想法,更是長久以來各種情緒起伏的核心因子。我想說的是,其實不需要其他人告訴你問題是什麼,你需要的只是一種能夠信賴的引導,透過不停地挖掘與整理,當那最核心的因子浮現時,情緒是那樣地清楚、道理是那樣地明白,你自己會認出它的。
晤談結束後,雖然我並不確定這樣的問題是不是真的有根除的可能,畢竟它已經是我長久以來行為處事的依據與準則了,但是心情上卻輕鬆了大半,因為我不再為了「不確定性」而苦惱、我知道我為什麼憂鬱。第一次會面能有這樣的成績,我想我真的很幸運。
第二次會面
但是那樣的憂鬱還在,它仍籠罩著我。雖然大概知道問題的根源,但我仍然懷疑這樣的問題是不是真的能被解決。上次的晤談對我來說已經算是一大突破了,我甚至不知道接下來的諮商該如何下去,或是有沒有必要下去。第二次會面時我並沒有準備太多,甚至有點抱著看好戲的心態:嗯,諮商已經讓我知道問題的大概輪廓了,但是它能解決它嗎?是啊,醫生,接下來您要怎麼作呢?也因此,當醫生要我談談小時候的經歷時,我差一點噗哧笑了出來。這真的是太心理治療了!問題不是都已經浮現出來了嗎?那還有必要經過這樣一道S.O.P.嗎?我支支唔唔地不知道從何說起,一方面是因為小時候的記憶過於模糊,另一方面不知道哪一個記憶片段才會和這次的晤談、我的困擾有關。我把我的問題反應給心理師,他要我不要想那麼多,他說,每一個人對小時候的記憶都是有限的,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留」下來記憶,只要它能被記住,往往對那個人具有某種意義,而我所要作的便是隨意地挑選一段被留下來的記憶就好,愈早愈好,不用擔心它是不是跟你現在的困擾有關。於是我挑選了一段。
就像是第一次晤談一樣,只要你隨意地在你的記憶(或是困擾)上開了一小段缺口,所有的情緒將以排山倒海之勢傾洩而出。然後,當你說到一半、當你能真正面對那個時候、那段記憶留給你的情緒時,一切都更為明暸了;你發現原來小時候的成長經歷,對於自己現在的情感、態度與行為,竟擁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那時的悲傷與歡樂,決定自己在面對某件事情時,會有什麼樣的情緒、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你會發現,現在自己各種的情緒、反應與行為,甚至是不經意的念頭,原來背後都擁有如此深厚複雜的經歷與緣由。這其實是相當激勵人心的,因為你知道,你的問題與困擾,並不是先天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個性與本質,而是逐年累積的經歷與行為模式;而正因為是後天的形塑,便代表了它是可以改變、可以調整、可以改善的。
再一次地,我幾乎是微笑著步出大門。雖然我的困擾仍然存在,但是兩次的晤談,讓我更加地認識它。它不再是莫名的憂鬱與煩悶,相反地,它的輪廓愈來愈清晰,它的根源漸漸地被定位清楚;它是可以被解釋的、甚至是可以被處理的。對目前(接受過兩次諮商)的我來說,能認識到這些,已經是相當令人振奮、令人滿足的了。我非常期待接下來的會面,不僅期待著我還能認識多少我原來不知道的自己,更期待透過這樣的認識、這樣的治療,最後,我的狀況能有所改善。
〔註〕在台灣,心理治療不論是在文化上或是在制度上,都不是那樣地貼近民眾的生活。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都會認為,只有重大心理疾患的困擾,比如說精神分裂、憂鬱症、躁鬱症、甚至自殺行為等,才有「必要」去看心理醫生。但是事實上,心理諮商在日常生活裡的應用範疇可以更為廣泛;小自生活上的困擾、戀情/婚姻的挫敗、失眠、工作能力的評估與調適等,大至疾患的治療、認識自我與生涯規劃,心理醫生都可以作為我們一個更安全的傾吐對象、營造一個輕鬆且真誠的對話空間、提供我們一個深入檢視各種自身情緒與念頭想法的機會。只是很可惜的,在目前的制度上,台灣民眾並沒有辦法在健保途徑下「直接」尋求諮商治療,而必須透過精神科門診,經由精神科醫生的評估之後,再轉介給心理醫生。簡單地說,我們在健保底下是沒有辦法直接「掛號」進行心理諮商的,因為醫院裡根本就沒有這一個科別讓你掛號。如果你想不經由精神科醫生的中介而直接尋求心理醫生的協助,目前你只能求助於坊間的私人心理門診,或是在少數幾家大醫院裡,以「自費」的方式進行諮商。我覺得,這樣的制度多少限制了心理諮商在台灣的推廣程度,是有必要加以改進的。
2007年9月12日 星期三
主要角色 : 小蛋

1. 生命的起源 (小蛋: 聽起來好神! 但那是說雞蛋 不是說我)
2. 怪異型人格,與衣著如出一轍 (小蛋: 對 !)
3. 人小志氣高 (小蛋: 對 !)
4. 感情豐富 (小蛋: 是啦 !)
5. 放假前兩天會有躁動傾向,行為舉止退化至兒童時期,時哭時笑… (小蛋: 我們必須向假日致敬!)
6. 哭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於孟姜女有過之而無不及….
(小蛋: 哪有!!!)
7. 富正義感 (小蛋: 沒錯 !)
秘密
--龐氏問卷 acting out (衝動) 分數=9 (小蛋: ㄟ滿分是幾分啊?)
標籤: 小蛋, 心HIGH革命,緣起不滅~, 革命成員角色介紹